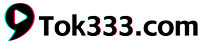责任编辑: izc19.com
在扶霞•邓洛普(Fuchsia Dunlop)写给几千年中国美食的情书“Invitation to a Banquet”(宴请)中,一些最不经意提到的内容最吸引人。比如,她曾在牛津——一个你意想不到的地方——为一次宴会烹饪了350条鸭舌;她还在乌鲁木齐的哈萨克族割礼仪式上第一次尝到了发酵骆驼奶;还有公元前7世纪齐国(今山东)国君齐桓公的御厨易牙据说拥有完美味觉,但也据说他为了取悦齐桓公把自己的儿子做成了肉汤。
如果是其他美食作家,可能被质疑用力过猛,但扶霞的学识之广、之深,以及极具感染力的热情,不会遭到此类质疑。20世纪90年代,她成为首位在成都四川烹饪高等专科学校(Sichuan Higher Institute of Cuisine)学习的外国人。自那以来,她通过写作、新闻报道和美食之旅,试图鼓励其他人尝试她这种冒险之旅来品尝世界上最伟大的美食之一。
“Invitation to a Banquet”并不是一本烹饪书,而是通过在一系列章节中解释关键食材和烹饪技术,讲述美食在中国文化、政治、宗教和生活方式中的核心重要地位。我们从这本书中知道了安吉竹笋配金华火腿,知道了一品锅(一种用上等食材调制的顶级汤,用扶霞的话说,“就像聆听交响乐的前奏”)。还有一篇短文介绍了“曲”的魔力,“曲”可以用来发酵从红酒到酱油等各种东西。我们还从书中发现了外来影响和后共产主义中国美食之间的复杂关系,具体体现在罗宋汤中。
正如偶尔为英国《金融时报》撰稿的扶霞揭示的那样,中国美食故事可以追溯到数千年前。周朝(公元前1046年至公元前256年)时期,食物在中国人的国家观念中如此重要,以至于国君的饮食以及国君在农业中的象征性角色都有严格规定,国君颁布的历书中也规定了必须进行的祈求庄稼丰收的季节性祭祀仪式。在此之前的几千年,中国的饮食文化建立在定居农业的基础上,首先出现的是小米,然后是南方的大米(可能在大约9000年前出现)和北方的小麦(大约4000年前出现)。中国核心区域发展出了涉猎范围和种类都无与伦比的美食,和利用每一种可用食材在相对稀缺的土地上养育大量人口的烹饪传统。
如今,从四川的辛辣到广东的清淡,各地的口味千差万别。但是,正如扶霞所说的那样,全国各地制作中餐宴席的目标都是相似的——厨师的目标是在菜品中将口味和口感完美融合,通常还要用更神秘的、将食与药的传统结合在一起的特色来平衡这些考虑。她提醒我们,在中国,如果你身体不舒服,医生会建议你食用适当的食物,让身体恢复平衡。
扶霞开发了一系列词汇,以应对传达中国美食中蕴含的众多价值观、抱负和经验的艰巨挑战——当然,从色香味的享受开始,但延伸到近乎色情的口感描述。她写道,中国美食视频的音轨中充满了“湿意、吧唧、咂巴和吮吸的声音”,而鸡睾丸的完美质地是“细腻光滑、极其软嫩,但又有一定的弹性”。
正如扶霞•邓洛普解释的那样,所有这些吮吸和吧唧声都有阴暗的一面——中国人坚信一切都可以食用。越稀有的东西越令人向往;与此同时,还有一种迷信认为,比方说,吃熊掌或虎仔,可以让食客获得这种动物的某些特性。正是这种信念导致中国富有的食客们无视动物保护禁令。
石首鱼的鱼鳔因其质地在中式菜肴中尤为珍贵。加利福尼亚湾的非法刺网捕鱼已经摧毁了石首鱼的种群,并将以石首鱼为食物来源的海洋中最小的鲸目动物小头鼠海豚推向灭绝的边缘。2017年,一艘中国渔船在加拉帕戈斯(Galápagos)海洋保护区被截获,船上有6000条已经死亡的鲨鱼;在苏格兰西海岸,经常会遇到一车又一车通过可疑方式捕捞的蛏子在夜间被打包准备发往香港。该书还承认,在过去40年的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中,中国的很多东西都消失了。
扶霞对中国美食的热情可能会导致令人不快的对比。英式烹饪当然是乏味的,但在本书的描述中,它比把一块肉旁边摆上煮过头的蔬菜强不了多少。更公平的比较应该是与整个欧洲相比,欧洲拥有相当多样的烹饪传统和完整的分类——比如奶酪制作——而这些在中国美食传统中几乎是缺失的。本人可能还会对她所说的中国公立学校的饭菜优于英国的说法提出质疑:上世纪70年代,我就读的上海复旦大学(Fudan University)的学生食堂是世界上最糟糕的美食体验之一。但这些都是次要的反对意见。
扶霞抱怨中国美食被理解得不够透彻和被低估是对的。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许多在世界其他地方开餐馆的移民自身并不是受过训练的厨师,他们调整了自己的菜品来迎合不了解中国美食的顾客们的口味。即使在今天,无知和偏见也造成了一种预期,即中餐在西方就应该便宜。这种预期正是这本扶霞将学识和激情完美地融合在一起的书要打破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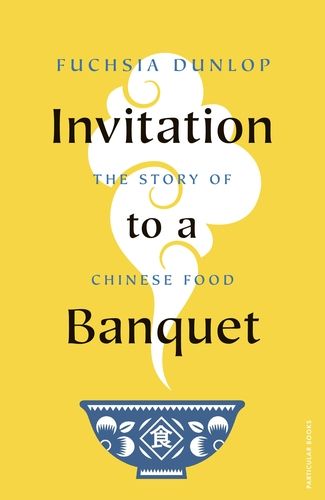
译者/何黎
文章编辑: izc19.com